ZDNLC
金牌會員
 
UID 408659
精華
0
積分 155
帖子 164
閱讀權限 100
註冊 2017-11-7
狀態 離線
|
 第七章
第七章
第七章
說了一會話,看看天色不早,莊之蝶還是硬了腿兒附在牛的肚子下用口吮
奶。
柳月瞧著有意思,嚷著她也要噙了牛的乳頭吮,才趴下身去,牛就四蹄亂
蹬,那麼一條毛尾像刷子一樣掃得她臉疼。
急一躲避,胳膊上的一件玉石鐲兒掉在地上就碎了,當下哭喪了臉,說這
玉鐲兒是那家女主人賞她的一個月的工錢,拾了半塊磚頭就砸在牛背上。
莊之蝶忙把她唬住,說:「我早瞧見了,那是蘭田次等玉,值不得幾個錢
的!你大姐有一個鐲兒,是菊花玉鐲,她胳膊太粗,也戴不上,我讓她送你!
」
柳月臉上綻了笑意,說:「這牛也太沒禮性。
你吃奶它就不動的,莫非前世你們還有什麼緣分?!」
莊之蝶說:「這真說不定,它讓你壞了一個玉鐲兒,也怕是前世你欠過它
的一筆小債!」
這話說著無意,柳月有心,聽了卻一天裡悶悶不樂,恍恍惚惚倒覺得自己
生前與這牛真有了什麼宿怨,晚上吃罷飯,自個便到城牆根去,剜了一大籃嫩
白蒿、螞蚱菜、苦芨條,說是明日一早牛再來了喂了吃。
牛月清說:「柳月心這麼好的,咱姐妹活該要在一處。
我就見不得人可憐,誰家死了人,孝子一放哭聲我眼淚就出來了。
門前有了討飯的,家裡沒有現成吃的,也要去飯館買了蒸饃給他。
去年初夏,天下著雨,三個終南山裡來的麥客尋不到活,蜷在巷頭屋簷下
避雨,我就讓他們來家住了一夜。
你莊老師一提起這些事就笑我,說我是窮命。」
柳月說:「大姐還算窮命呀,有幾個像你這般有福的呢!連那賣奶的劉嫂
也說,你家女主人銀盆大臉,鼻端目亮,是個娘娘相哩!」
牛月清說:「他是說我骨子裡是窮命。」
柳且說:「這麼說也是的。
以前沒到你們家,真想像不出你們吃什麼山珍海味的,來了以後,你們竟
喜歡吃家常飯,平日菜也不要炒,也不要切,白水煮在鍋裡,就是我們鄉下人
也不這麼吃的。」
牛月清說:「這樣營養好哩,別人都知道你莊老師愛吃玉米麵糊糊煮洋芋
的,哪裡卻曉得每頓我要在他碗裡撒些高麗參未兒!」
柳月說:「可你總是不該缺錢花呀,穿的怎麼也不見得就時興,化妝品也
還沒我以前的那家媳婦的多!」
牛月清就笑了:「你莊老師就這麼吩叨我,你也這般說呀,真是我邋遢得
不像樣了?」
柳月說:「這倒不是,但像你這年齡正是收拾打扮的時候,你又不是沒有
基礎,一分收拾,十分人材就出來了!」
牛月清說:「我不喜歡今日把頭髮梳成這樣,明日把頭髮又梳成那樣,臉
上抹得像戲臺上的演員。
你莊老師說我是一成不變。
我對他說了,我變什麼?我早犧牲了我的事業,一心當個好家屬罷了,如
果我打扮得妖精一樣,我也像街上那些時興女人,整日去逛商場,浪公園。
上賓館喝咖啡,進舞場跳迪斯可,你也不能一天在家安生寫作了!」
柳月一時語塞,停了一會兒,卻說:「大姐,莊老師寫的那些小說你也讀
嗎?」
牛月清說:「我知道他都是編造的,讀過幾部,倒覺得入不到裡邊去。」
柳月說:「我是全讀了的,他最善於寫女人。」
牛月清說:「人都說他寫女人寫得好,女人都是菩薩一樣。
年前北京一個女編輯來約稿,她也這麼說,認為你莊老師是個女權主義者
。
我也不懂的,什麼女權不女權主義。」
柳月說:「我倒不這樣看,他把女人心理寫得很細。
你上邊說的那些話,我似乎也在哪一部書裡讀到過的。
我認為莊老師之所以那麼寫女人都是菩薩一樣的美麗、善良,又把男人都
寫得表面憨實,內心又極豐富。
卻又不敢越雷池一步,表現了他是個性壓抑者。」
牛月清說:「你莊老師性壓抑?」
說過了就笑了一下,點著柳月的額頭說:「該怎麼給你說呢?你這個死女
子,沒有結婚,連戀愛也沒戀愛,你知道什麼是性壓抑了?!不說這些了,柳
月,你把剜來的草淋些水兒放到廁所房裡陰著去,大熱天的在院子裡曬蔫了,
明日牛也吃著不新鮮。」
柳月去把青草淋了水放好,過來說:「大姐,說到牛,我心裡倒慌慌的。
我們村發生過一宗事,好生奇怪的。
是張來子爹在世的時候,光景不錯,借給了張來子舅舅八十元,來子他爹
一次挖土方,崖塌下來被砸死了,來子去向他舅舅討帳,他舅舅卻矢口否認。
兩人好是一頓吵,他舅舅就發咒了,說要是他賴帳死了變牛的,張來子聽
他這麼說也就不要帳了。
這一年三月天,張來子家的牛生牛犢子,牛犢子剛生下來,門口就來人報
喪,說是他舅舅死了,來子就知道這牛犢是他舅舅脫變的,倒一陣傷心。
以後精心餵養牛長大,也不讓牛耕地拉磨。
有一天拉了牛去河畔飲水,路口遇著一個擔瓦罐的鄰村人,牛就不走了。
來子說:舅呀舅呀,你怎麼不走了呢?那人覺得奇怪,怎麼把牛叫舅舅?
來子說了原委,那人才知道他舅舅死了。
那人是認識來子舅舅的,倒落了幾顆眼淚,想牛卻後蹄一踢,踢翻了罐擔
子,罐就全破碎了。
來子忙問這瓦罐值多少錢,那人說四十元的。
來於要賠,那人卻說:來子,不必賠了,你舅舅生前我是借過他四十元的
,他這是向我要帳的呢!大姐,這奶牛壞了我的玉鐲兒,莫非我真的就欠了它
帳的?!」牛月清說:「就是欠帳,這不是也還了嗎?你莊老師也說過了,我
的菊花玉鐲放著也是白放,你就戴著吧。」
當下取了戴在柳月手腕上。
也活該是柳月的,玉鐲兒不大不小戴了正合適。
柳月就以後常縮了袖子,偏露出那節白胳膊兒。
一日早晨。
柳月扶了莊之蝶在院門口吃了牛奶,又喂了奶牛的青草,牛月清就上班去
了。
莊之蝶在院門口一邊同劉嫂說話,一邊看著奶牛吃草,柳月就先回了家。
閑著沒事、便坐在書房裡取了一本書來讀,自莊之蝶住到這邊來,特意讓
從文聯大院那邊搬了許多書過來,柳月搬書時什麼文物古董都沒拿,卻同時將
那唐侍女泥塑帶過來,就擺在書房的小桌上。
也是有了她生前欠了牛的債的想法後,便也常記起初來時眾人說這侍女酷
像她,她也就覺得這或許又是什麼緣分兒的,於是每日來書房看上一陣。
這麼讀了一會兒書,不覺就入迷了,待到莊之蝶進來坐在桌前寫東西,她
趕忙就要去廳室。
莊之蝶說:「不礙事的,你讀你的書,我寫我的文章。」
柳月就坐下來又讀。
但怎麼也讀不下去了,她感覺到這種氣氛真好:一個在那裡寫作,一個在
這裡讀書,不禁就羞起來,抬頭看著那小桌上的唐侍女,欲笑未笑、未笑先羞
的樣子,倒也覺得神情可人。
這麼自己欣賞著自己,坐著的便羡慕了站著的,默默說:我陪著他只能這
麼讀一會兒書,你卻是他一進書房就陪著了!噘了嘴巴,給那侍女一個嗔笑。
待到莊之蝶說:「柳月,你倆在說什麼活?」
柳月就不好意思起來,說:「我們沒說話呀!」
莊之蝶說:「我聽得出的,你們用眼睛說話哩!」
柳月臉緋紅如桃花了,說:「老師不好好寫文章,倒偷聽別人的事!」
莊之蝶說:「自你來後,大家都說這唐侍女像你的,這唐侍女好像真的附
了人魂似的,我一到書房看書寫作,就覺得她在那裡看我,今日又坐了個活唐
侍女,我能入得了文章中去嗎?」
柳月說:「我真的像這唐侍女?」
莊之蝶說:「她比你,只是少了眉心的痔。」
柳月就拿手去摸眉心的痔,卻摸不出來,便說:「這痔不好吧?」
莊之蝶說:「這是美人痔。」
柳月嘎地一笑,忙聳肩把口收了,眼睛撲撲地閃,說道:「那我胳膊上還
有一顆呢!」
莊之蝶不覺就想起了唐宛兒身上的那兩顆痔來,一時神情恍惚。
柳月說著將袖子往上綰,她穿的是薄紗寬袖,一綰竟縮到肩膀,一條完整
的肉長藕就白生生亮在莊之蝶面前,且又揚起來,讓看肘後的痔,莊之蝶也就
看到了胳肢窩裡有一叢錦繡的毛,他於是接收了這支白藕,說聲:「柳月你這
胳膊真美!」
貼了臉去,滿嘴口水地吻了一下。
窗外正起了一群孩子的歡呼聲,巷道裡一隻風箏扶搖而起了。
牛在看見柳月抱了嫩草給它的時候,牛是感激地向柳月行了注目禮的。
在牛的意識裡,這小女人似乎是認識的,甚至這雙仁府,也是隱隱約約有
幾分熟悉。
它仔細地回憶了幾個夜晚,才回憶起在它另一世的做牛的生涯裡,是這雙
仁府甜水局一十三個運水牛馱中的一個,而這小女人則是當初水局裡的一隻貓
了。
是有過那麼一日,十三頭牛分別去送水,差不多共是送出去了五十二桶水
,收回了一百零四張水牌子,但這只貓卻在牛的主人坐下吃煙打噸的時候叼走
了兩個水牌去城牆根玩耍丟掉了,結果牛和它的主人受了罰。
後來呢,它的前世被賣掉在了終南山裡,轉世了仍然是牛,就在山裡;貓
卻因為貪食,被別人以一條草魚勾引離開了水局,剝皮做了冬日取暖的圍脖,
來世竟在陝北的鄉下為人了。
牛的反芻是一種思索,這思索又與人的思索不同,它是能時空逆溯,可以
若明若暗地重現很早以前的圖像。
這種牛與人的差異,使牛知道的事體比人多得多,所以牛並不需要讀書。
人是生下來除了會吃會喝之外都在愚昧,上那麼多的學校待到有思想了,
人卻快要死了。
新的人又齊始新的愚昧,又開始上學去啟蒙,因此人總長不高大。
牛實在想把過去的事情說給人,可惜牛不會說人話,所以當人常常志卻了
過去的事情,等一切都發生了,去翻看那些線裝的志書,不免浩歎一句「歷史
怎麼有驚人的相似」,牛就在心裡嘲笑人的可憐了。
現在,它吃完了嫩草,被劉嫂牽著離開了雙仁府沿街巷走去,毛尾就搖來
搖去扇趕著叮它的牛虻,不知不覺地又有它的心思了。
在這一來世裡,它是終南山深處的一頭牲口,它雖然來到這個古都為時不
短,但對於這都市的一切依然陌生。
城市是什麼呢?城市是一堆水泥嘛!這個城市的人到處都在怨恨人太多了
,說天越來越小,地面越來越窄,但是人卻都要逃離鄉村來到這個城市,而又
沒有一個願意丟棄城籍從城牆的四個門洞裡走出去。
人就是這樣的賤性嗎?創造了城市又把自己限制在城市。
山有山鬼,水有水魅,城市又是有著什麼魔魂呢?使人從一村一寨的誰也
知道誰家老爺的小名,誰也認得土場上的一隻小雞是誰家飼養的和睦親愛的地
方,偏來到這一家一個單元,進門就關門,一下子變得誰都不理了誰的城裡呢
?街巷裡這麼多人,你呼出的氣我吸進去,我呼出的氣你吸進去,公共汽車上
是人擠了人。
影劇院裡更是人靠了人,但都大眼瞪小眼地不認識。
如同是一堆沙子,抓起來是一把,放開了粒粒分散,用水越攪和反倒越散
得開!從有海有河的地方來偏要游泳公園中的人造湖,從有山有石的地方來偏
要攀登公園裡的假山。
可笑的是,在這個用四堵高大的城牆圍起來的到處組合著正方形、圓形、
梯形的水泥建築中,差不多的人都害了心臟病、腸胃病、肺病、肝炎、神經官
能症。
他們無時不在注意衛生,戴了口罩,製造了肥皂洗手洗腳,研製了藥物針
劑,用牙刷刷牙,用避孕套套住陰莖。
他們似乎也在思考:這到底是怎麼啦?不停地研究,不停地開會,結論就
是人應該減少人,於是沒有不談起來主張一個重型的炸彈來炸死除了自己和自
己親人以外的人。
牛就覺得發笑了。
牛的發笑是一種接連的打噴嚏,它每日都會有這麼一連串的噴嚏的。
但牛又在想了,牛在想的時候也是顛來倒去地掂量,它偶爾冒上來的念頭
是自己不理解人,不理解擁擠著人的這個城市,是不是自己不是人也沒有註冊
於這個城市戶籍的緣故?自己畢竟是一頭牲口,血液裡流動的是一種野性,有
著能消化草料的大的胃口,和並不需要衣飾的龐大的身軀?但是,牛堅信的是
當這個世界在混飩的時候,地球上生存的都是野獸,人也是野獸的一種。
那時天地相應,一切動物也同天地相應,人與所有的動物是平等的;而現
在人與蒼蠅、蚊子、老鼠一樣是繁殖最多的種族之一種,他們不同於別的動物
的是建造了這樣的城市罷了。
可悲的,正是人建造了城市,而城市卻將他們的種族退化,心胸自私,度
量窄小,指甲軟弱只能掏掏耳屎,腸子也縮短了,一截成為沒用的盲腸。
他們高貴地看不起別的動物,可哪裡知道在山林江河的動物們正在默默地
注視著他們不久將面臨的未日災難!在牛的另一種感覺裡,總預感了這個城市
有一天要徹底消亡的,因為靜夜之時,它發現了這個城市在下陷,是城市每日
大量汲取地下水的緣故,或是人和建築越來越多,壓迫了地殼的運動,但人卻
一點也不知道,繼續在這塊地上堆積水泥,繼續在抽用地下水,那使他們沾沾
自喜的八水繞西京的地理,現在不是幾水已經乾涸了嗎?那標誌著這個城市的
大雁塔不是也傾斜得要倒塌了嗎?到那一日,整個城市塌陷下去,黃河過來的
水或許將這裡變成一個水澤,或者沒有水,到處長滿了蒿草。
那時候,人才真正知道了自己的過錯;知道自己過錯了,也成了水澤中的
魚鱉,也成了啃吃蒿草的牛羊豬狗;那就要明白了這個世界上野性是多麼與天
地同一,如何去進行另一種方式的生存了。
這牛想到這裡,只覺得頭腦發疼,它雖然在大街上恍恍惚惚地走著,感覺
良好地以為自己是個哲學家了,但它懊喪上天賦予自己的靈性並不怎麼多,思
緒太雜太亂,一作長思考就頭疼,甚至也常常靈魂出殼,發生錯覺,潛意識裡
是拉著一張犁的,一張西漢或是開元年間的鈍犁,就在屎殼郎般的小汽車當中
被圍困了,莫名其妙地望著不斷拔節的鞋後跟,找不到耕耘的田野。
它對於自己的智慧的欠缺和不由自主的走神兒就長聲歎息了。
於是,索性在劉嫂牽了它經過一座公園的長牆外的小路上走著時,就扭了
頭去嚼吃那牆根叢生的酸棗刺。
人吃辣子圖辣哩,牛吃棗刺圖紮哩,氣得劉嫂不停地用樹棍兒敲打了它的
屁股說:「走呀,走呀,天不早了呀!」
牛月清見莊之蝶腳傷遲遲不好,每日換了藥膏就不讓他多活動,特意給文
聯大院的門房韋老太婆和雙仁府這邊巷口的人家叮囑了:任何來人找莊之蝶,
都說人不在家,也不要告訴家的門牌號數,又私下吩咐了柳月,故意將電話聽
筒放不實確,使外界無法把電話打通進來。
這樣一來,旁人也倒罷了,苦得周敏如熱鍋上的螞蟻。
那天下午,他來找到師母,要告知的是文化廳研究宣傳部長的三條指示,
決定讓周敏和雜誌社去向景雪蔭賠禮道歉。
周敏和李洪文去見景雪蔭,景雪蔭高仰了頭,只拿了指甲油塗染指甲,塗
染過了還抬起來,五指複開複合地活動,一句話也不說。
周敏當即一口唾沫呸在地上,拉門出來了。
李洪文匯報了廳裡,廳長說:「那就這樣吧,她不理你們是她的事。
別的指示我們可以先搪塞上邊。
可第三條,在下期刊物上發嚴正聲明卻要照辦的。
你們擬出文來,讓我看看。」
周敏就為了擬此文的用字遣詞來討莊之蝶的主意;但莊之蝶在人大會議上
,無法進得古都飯店,第二天一早時間已來不及,只好和鐘唯賢自擬了交上去
。
廳長又讓景雪蔭過目,景雪蔭卻不同意了,嫌用詞含糊,必須寫上「嚴重
失實,惡意誹謗」,周敏和鐘唯賢就不同意,雙方僵起來。
廳長便將擬文呈報宣傳部,俟等上邊裁決。
周敏又是第三次第四次去文聯大院和雙仁府兩邊尋找莊之蝶,門房都說人
是不在的,給兩邊的家掛電話,總是忙音,心裡就犯了疑惑,以為莊之蝶是不
是不管此事了?他是名人,又上下認識人多,他若撤手不管,自己就只有一敗
塗地的結果了,不免在家罵出許多難聽話來。
唐宛兒卻另有一番心思,忐忑不安的是她去了幾次古都飯店,莫非露了馬
腳,被牛月清得知,莊之蝶才故意避嫌躲了他們?想起那日傍晚,她幽靈般地
到七零三房間去,門是虛掩著,卻沒見到莊之蝶。
呆了半個小時又不敢多呆,在走廊裡轉了幾個來回再走下來,後來又轉到
樓的後邊巷道,數著那第三個窗口看有沒有燈光亮起,直是腳疼脖酸地守望了
兩個小時,那視窗還是黑的,方灰不遝遝轉身回去。
莊之蝶約定好好的知道她要去的,為什麼人卻不在?現在猜要麼是走了風
聲,要麼是牛月清也去過了飯店,便將莊之蝶強逼了回家去睡?要麼還是那飯
店的服務員打掃房間,在莊之蝶的床單上、浴盆中發現了長的頭髮和曲卷了的
毛兒,有了嘰嘰咕咕?心裡有事,身子也懨懨發困,一連數日不出門,只把肥
嘟嘟一堆身子呆在床上和沙發裡看書。
書是一本叫《古典美文叢書》,裡邊收輯了沈三白的《浮生六記》和冒辟
疆寫他與董小宛的《翠瀟庵記》。
還有的一部分是李漁的《閒情偶記》中關於女人的片斷。
唐宛兒先讀的是李漁的文章,讀到女人最緊要的是有「態」,便對「態」
是什麼不甚了了,待看到有態了三分人材便會有七分魅力,無態了七分人材也
只有三分魅力,態于女人,如火之有焰,燈之有光,珠玉有寶氣,她便連聲稱
是,覺悟道:「這態不就是現在人說的氣質嗎?」
就自信於自己絕對是有態的人。
往後又讀了《翠瀟庵記》更是愛煞了那個董小宛,不禁想到:「這冒辟疆
是才子,莊之蝶也是才子,冒辟疆纏纏綿綿一個情種,莊之蝶又何嘗不是如此
,而自己簡直就是那個董小宛了嘛,天下事竟有這般奇妙,自己也是有個「宛
」字的!於是猛一回首,便感覺裡有個董小宛飄然向自己走來,忍不住就嫣然
一笑了。
然後望著窗外的梨樹,想著這梨樹在春天該多麼好,舉一樹素白的花,或
者是冬天,頂那麼厚的雪,我在屋子裡聽下雪的聲音,莊之蝶踏著雪在院牆外
等我,那牆裡樹和牆外的他一樣白吧?現在是夏天,沒有花,也沒有雪,梨樹
純有葉子也是消瘦,消瘦得如她唐宛兒的時光。
唐宛兒這麼恍恍若夢,低了頭又去讀書。
書上寫到下雨,起身來到院子裡,院裡果然淅淅瀝瀝有了雨,面對了梨樹
和一樹無人知道的雨,就死了心地認定這梨樹是莊之蝶的化身,想,莊之蝶原
來是早在她搬住到這院子的時候就在這裡守候了她嗎,遂緊緊抱了一會梨樹,
回到屋裡,一滴眼之雨珠就落在了翻開的書上。
白日就這麼捱了過去,到了晚上,周敏還是遲遲不能回來,相隔不遠的清
虛庵的鐘聲,把夜一陣陣敲涼。
視窗的一塊玻璃早已破裂,是用白紙糊的,風把紙又吹出了洞,嘩啦嘩啦
地響。
唐宛兒突然驚悸了一下,感覺裡莊之蝶就在院門夕徘徊。
她穿了拖鞋便往外跑,下臺階時頭上的髮卡掉了,頭髮如瀑一樣灑下,她
一邊走一邊彎腰撿髮卡,撿了幾次未能撿到,還是過去開了院門,院門夕外卻
空寂無人,又左右看了看街巷。
也許,他是在哪一個暗處招手,看了許久才發現那不是他,是風。
木呆呆返回來,清醒了莊之蝶是沒有來,好多好多天日也沒有來了,或許
永遠也不會來了,就哽咽有聲,滿臉淚流,歎其命運不濟。
這麼一哭,不能收住,又將長時間裡沒有泛上來的思子之情襲了心間,越
發放聲號啕。
計算日子,再過三日竟是兒子三歲的生日,就不管了周敏回來不回來,再
次開了門出去,直喊了一輛蹬三輪車的夜行人,掏三元錢讓拉她去鐘樓郵局,
給潼關的舊家發了電報,電報是發給兒子的,寫了「願我兒生日快樂。」
一路哭泣回來就睡了。
周敏夜闌回來,見冰鍋冷灶,也不拉燈,問婦人怎麼啦,拉了電燈,揭開
被子,疑惑婦人眼怎麼腫得如爛桃一般,就發現枕邊的電報收據,上邊寫有潼
關。
急問了原由,不覺怒從心起,摑了婦人一個耳光。
唐宛兒跳下床來,竟不穿一絲一縷,上來就揪周敏的頭髮。
罵道:「你打我?你敢打我?!孩子那麼小,沒了她娘,三歲生日了,我
就是狼也該發七個字的問候吧?」
周敏說:「你腦殼進水了嗎?是豬腦殼嗎?一紙電報抵什麼屁用!他收了
電報,必要查電文從哪兒發的,上邊有西京字樣,你這不是成心要他知道你我
在哪兒嗎?」
唐宛兒說:「他知道了又咋?西京大得如海,他就尋著來了不成?」
取了鏡來照臉,臉上是胖起來的五個滲血的指印,唐宛兒又過來揪周敏的
頭髮,揪下一團,又哭了:「你那麼英雄,倒怕他來尋到你;那你還是怯他嘛
,你這麼個膽小樣兒,何必卻要拐了他的老婆,像賊一樣地在西京流浪?!跟
你流浪倒也罷了,你竟能打我!在潼關他也不敢動我一個指頭的,你這麼心狠
,你來再一掌拍死我算了!」
周敏瞧見婦人臉腫得厲害,想這女人也是跟了自己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就後悔自己下手太重了,當下跪下來,抱了她的雙腿,求她饒恕,又抓了她的
手讓在自己臉上打。
周敏是有一套哄女人的本事,也是真心實意痛恨自己,婦人也就不哭。
周敏見她擦了眼淚,便上去抱了她親,用手搔她的身子,一定要讓她笑了
才說明她是饒恕了他。
原來婦人有個秘密,就是身上癢癢肉多,以前周敏取笑過她癢癢肉多是喜
歡他的男人多。
莊之蝶也這麼搔過她,取笑過她,於吟吟浪笑裡給了她更強有力的壓迫和
揉搓。
這陣禁忍不住,就笑了一下,周敏方放了心去廚房做飯,又端一碗給婦人
吃了,相安無事睡下。
莊之蝶在家悶了許多天日,總覺得有一種無形的陰影籠罩了自己,想發火
又無從發起,恨不能出門散心,也不見一幫熟人來聊,終日看看書,看過全然
忘卻,就和柳月逗些嘴兒說話。
兩人已相當熟膩,早越了小保姆和老師的界限。
莊之蝶讓柳月唱個歌兒,柳月就唱。
陝北的民歌動聽,柳月唱的是《拉手手》,歌詞凡是:你拉了我的手,我
就要親你的口;拉手手,親口口,咱們兩個山屹嶗裡走。
莊之蝶聽得熱起來,柳月卻臉色通紅跑進老太太那間臥室裡將門關了。
莊之蝶一拐一瘸過去推門推不開,叫:「柳月,柳月,我要你唱哩!」
柳月在門裡說:「這詞不好,不要唱的。」
莊之蝶說:「不唱就不唱了,你開了門嘛!」
柳月不言語了,停了一會,卻說:「莊老師,你該笑我是學壞了?!」
莊之蝶說:「我哪裡這樣看你?」
就直推門。
柳月在裡悄聲拉了門閂,莊之蝶正使了勁,門猛地一開,人便倒在地上,
腳疼得眉眼全都錯位了。
嚇得柳月忙蹴下看他腳,嚴肅了臉兒說:「這都怪我,大姐回來該罵我,
攆了我哩!」
莊之蝶卻在柳月的屁股上擰了一下,說:「她哪裡知道?我不讓你走,你
是不能走的!」
就勢把柳月一拉,柳月一個趔趄險些腳踩了莊之蝶身子,才一邁腿,竟跌
坐在莊之蝶脖子上,小腹正對了嘴臉,莊之蝶就把她雙腿抱死。
柳月一時又驚又羞。
莊之蝶說:「這樣就好,讓我好好看看你!」
柳月的短衫兒沒有貼身,朝上看去,就看見了白胖胖的兩個大乳,乳頭卻
極小,暗紅如豆,莊之蝶說:「你原來不戴乳罩?!」
騰了手就要進去,柳月扭動著身子不讓他深入口口口口口口(作者刪去二
十五字)說:「你什麼女人沒見過,哪裡會看上一個鄉里來的保姆?我可是一
個處女哩!」
一撥手,從莊之蝶身上站起來,進廚房做飯了。
莊之蝶落個臉紅,還躺在地板上不起來,想自己無聊,怎麼就移情于柳月
?!兀自羞恥,卻聽得廚房裡柳月又唱了,唱的是:
大紅果果剝皮皮,外人都說我和你。
其實咱倆沒那回事,好人擔了個賴名譽。
夜裡,夫婦二人在床上睡了,說家常話,自然就說到柳月。
牛月清問:「柳月今日怎麼穿了我那雙皮鞋?我先不經意,她見我回來了
就去換了拖鞋,臉紅彤彤的,我才發現的。」
莊之蝶說:「她早晨洗了她的鞋,出門要買菜時沒有鞋穿,我讓她穿了的
,回來她怕是忘了換。
這女子倒是好身架,穿什麼都好看,你那麼多鞋的,那雙就讓她穿了吧。
」
牛月清說:「要給人家鞋,就買一雙新的送她。
我那雙也是新穿了不到半個月,送了她卻顯得是咱給她的舊鞋。」
莊之蝶說:「夫人好賢慧。
那我明日就給了她錢讓她自個去買一雙是了。」
牛月清說:「你倒會來事!」
就又說,「我還有一件事,想起來心裡就不安的,今日清早去上班,在竹
笆市街糖果店裡看有沒有好糖果兒,那個售貨員看了我半天,問道:你是不是
作家莊之蝶的夫人?我說是的,有什麼事?她說我在一份雜誌上看見過你夫妻
的照片,你家裡是不是新雇了一個保姆?我說是呀,是個陝北籍的叫柳月,模
樣兒水靈;誰看著也不會認作是鄉下的女子。
她說,人皮難背。
我問說這話有什麼由頭,莫非柳月來這店裡買糖果,是多找了錢沒吭聲就
走了嗎?那售貨員說柳月以前在她家當保姆的,就咬了牙齒發恨聲:這保姆可
坑了我了,我從勞務市場領她去我家看孩子,她不知怎麼就打聽到你們家,鬧
著要走,要走我也不能強留不放,只是勸她等我找到新的保姆了再走吧。
這不,一天下班回來,孩子在家裡嗚嗚哭,她人不見了,桌上留個條兒說
她走了!她攀了你們高枝兒了,害得我只好在家看了孩子半個月,工資獎金什
麼也沒了,她倒多拿了我的半月保姆費。
售貨員說了這一堆,我沒吭聲,信了她怕事實不確冤了柳月,不信吧,心
裡總是不乾淨,像吃了蒼蠅。
你說是實是假?」
莊之蝶說:「柳月不會心毒得那樣的,怕是柳月能幹,那家捨不得她走;
她走了那家人倒嫉恨了咱,說些挑撥話兒。」
牛月清說:「我也這麼想過。
可這女子模樣好,人也乾淨俐落,容易討人歡心,我待她好是我的事,你
別輕狂著對她好呀!」
莊之蝶說:「你要這麼說,明日我就辭了她!」
牛月清說:「你知道我不會讓她走的,你說放心的話!」
說著就蠕動了身子,說她要那個,莊之蝶推說腿是這樣,是要我命了嗎?
牛月清伸了伸腳腿了,說:「那你要記著太虧了我!」
趴下身瞌睡去了。
第二天,牛月清去上班,幹表姐卻把電話打到她的單位,牛月清自然問她
娘在那邊怎麼樣?幹表姐說啥都好的,早上一碗半紅豆兒稀飯,中午吃半碗米
飯;飯是不多,菜卻是不少的。
你姐夫從渭河捕了三條魚,孩子們都不准吃,只給老姑吃。
晚上是兩個雞蛋蒸一碗蛋羹的,還有一杯鮮羊奶。
老姑是胖了,也白了,只是擔心家裡的醋甕兒沒人攪搗,讓我給你說,別
只捂著甕蓋兒讓壞了。
再就是啥叨沒個收放機,不能見天聽戲的。
牛月清說,娘這麼愛聽戲的,她年輕時就見天坐戲園子。
也便說了這邊的事,譬如醋沒壞的;娘的幾雙舊鞋刷洗晾乾了,收拾得好
好的;那個王婆婆是來過幾次,還送了老太太一副黃布裹兜兒。
末了,隨便也把莊之蝶的腳說了一句。
湊巧,這個中午他們單位的領導要去渭河灘一帶為職工採買一批便宜鮮羊
肉,牛月清就匆匆回文聯大院那邊取了一部袖珍收放機和兩盤戲曲磁帶,要求
領導一定去鄧家營,打聽她幹表姐的家,把東西捎過去。
但是,牛月清中午回來,老大太卻已經在雙仁府這邊的家裡了。
一問原委;是幹表姐打完電話,順嘴把莊之蝶的腳傷說了,老太太就立馬
三刻坐不住要回,幹表擔奈何不了她,坐公共汽車就送了來,老太太查看了莊
之蝶的傷,並沒有說什麼,只嘟嚷著柳月被子疊得不整齊,桌子上的瓶子放的
不是地方,窗臺上的花盆澆水太多,牆角頂上的那個蜘蛛網怎麼就挑了?柳月
不敢言語。
到了晚上,柳月和老太太睡一個房子,老太太依舊以棺材為床,半夜裡卻
在說話。
柳月先以為是在給她說的,偏裝睡不理。
老太太卻越說越多,幾乎是在和誰爭吵,一會軟下來勸什麼,一會兒又惡
了聲嚇唬,且抓了枕頭去擲打,柳月睜眼看了,黑乎乎的什麼都沒有,就害怕
起來,過來敲夫人的臥室門。
莊之蝶和牛月清起來,過去問娘,是娘作噩夢嗎?老太太說:「你們這一
喊,他們倒都走了,我正好說歹說著的。」
牛月清說:「他們是誰?」
老太太說:「我哪裡知道?剛才我看著進來了幾個,手裡都拿著棍子,就
知道又是來磕之蝶的腿了。
這是哪兒來的,無冤無仇的磕我女婿什麼腿?」
牛月清說:「娘又說鬼了。」
嚇得柳月臉就煞白,牛月清又怨恨起來:「娘,不要說了,什麼人呀鬼呀
的,只嚇著我們!」
莊之蝶說:「你讓她說。」
就問老太太:「娘,娘,你嚇唬住他們了?」
老太太說:「這都是些惡鬼,哪裡肯聽我的?你明日去孕璜寺和尚那兒要
副符來,現在城裡到處是惡鬼,只有那和尚治得住的。
要了符回來,一張貼在門框上,一張燒了灰水喝下,你那腿就好了。」
莊之蝶說:「明日我就去孕磺寺,你好生睡吧。」
讓柳月也去睡。
柳月不肯,就睡了客廳沙發上。」
天明起來,牛月清去上班了,柳月眼泡腫脹,自然是一宿沒能睡好,安排
用過了牛奶、酥餅、茶飯,老太太翻出一塊布來又要做一個新的遮面巾,柳月
要幫她做,老太太看不上她的針線活,柳月就來書房和莊之蝶說話。
老太太一見他們說話,就仄了頭,眼睛從老花鏡的上沿來看,說:「之蝶
,你不是說要去孕磺寺嗎?」
莊之蝶說:「我知道的。」
去廁所小解了回來坐在客廳,看柳月立在廚房門上掛洗晾乾了的門簾兒。
昨日給的錢新買的高跟皮鞋柳月穿了,並不穿襪子,反倒另是一番韻味,
偏又是穿了一件黑色短褲,短褲緊緊地繃在身上,舉手努力把門簾往門框上的
釘頭上掛,腿腰挺直,越發顯得體態優美。
莊之蝶說:「柳月,你光腳穿這皮鞋真好看的。」
柳月還在掛門簾,說:「我腿上沒有毛的。」
莊之蝶說:「鞋尖夾趾頭不?」
柳月說:「我腳瘦。」
莊之蝶說:「你大姐腳太肥的,穿什麼樣鞋一星期就沒了形狀,這倒還罷
了;這些熟人裡腳不好的是夏捷,大拇趾根凸一個包的,什麼高跟中跟的鞋一
滿穿不成。
你注意了沒有,她坐在那兒,腳從不伸到前面來的。」
柳月就把一條腿翹起來,低了眼去看,莊之蝶卻一手將那腳握了,將臉貼
近,皺了鼻子聞那皮革的味和腳的肉香。
柳月雙手還在門框上,趕忙來收腿,又被親了一口,腿腳回到地上只覺得
癢,癢得臉也紅了。
莊之蝶卻裝得並不經意的樣子,又說這皮鞋式樣真是不錯的。
柳月見他這樣,臉也平靜下來,說:「你個男人家,倒注意女人的腳呀鞋
呀的?給誰說誰都不信的。」
莊之蝶說:「種地要種好地邊子,洗鍋要洗淨鍋沿子,女人的美就美在一
頭一腳,你就是一身破衣裳,只要有雙好鞋,精氣神兒就都提起來了。
唐宛兒就懂得這些,她才是講究她的頭上的收拾,活該也是她的頭髮最好
,密盈盈的又長又厚,又一半呈淡黃色,你幾時見她的髮型是重樣的?可你總
是紮個馬尾巴的!」
柳月說:「你知道我為啥紮馬尾巴?我是沒個小皮包兒,夏天穿裙子短衫
沒口袋,出門了擦汗的帕兒不是別在裙帶上,就用帕兒紮了那頭髮,要用時取
著方便。」
莊之蝶說:「那你也不說,我給你錢去買了包兒。
我現在才明白,街上的女人都挎個包,原以為裡邊裝有錢,其實是手帕、
衛生紙和化妝品!」
柳月就嘿嘿地笑。
老太太聽他們這邊說話,就又說:「之蝶,都什麼時候了,你還不去孕磺
寺嗎?」
莊之蝶給柳月擠擠眼,說:「就去,就去。」
心裡想,牛月清為什麼把我的腳傷告訴老太太,又讓老太太回來,是怕我
在家閑著只和柳月說話,說出個感情來哩?!心裡就又一陣發悶,頭皮發麻,
渾身也是這麼癢那麼癢的。
給孟雲房撥了電話,讓他去孕璜寺見智祥大和尚要副符。
打電話時才發現電話線壓在聽筒下邊,就說:「我說這麼多天,我不得出
去,也沒有個電話打進來,原來聽筒沒放實!柳月,這是你幹的?」
柳月瞞不過,才說了牛月清的主意。
莊之蝶就發了火:「靜養,靜養,那怎麼不送我去了監獄裡養傷?!」
柳月說:「這我得聽大姐的。」
莊之蝶說:「聽她?她盼不得我雙腿都斷了才好放心!」
柳月說:「大姐倒是好心,你這麼說倒屈了她。」
莊之蝶說:「她只知道給你吃好穿好身體好,哪裡又知道人活著還活一種
精神哩!別瞧她什麼事滿不在乎的樣兒,其實心才小的,誰也防著。」
柳月就問:「她也防我?」
莊之蝶沒有言語,扶牆走到書房獨坐了生氣。
孟雲房半晌午就來了,果然拿了符帖,直罵莊之蝶腳傷了這麼多天日竟不
對他吭一聲,平日還稱兄道弟地親熱,其實心裡生分,在眼裡把他不當個有用
的人看的。
莊之蝶忙解釋骨頭裂得並不十分厲害,只是拉傷了肌腱三天五天消不了腫
,告訴你了,白害擾得人不安寧,不僅是沒告訴你,所有親戚朋友一概不知的
。
孟雲房說:「害擾我什麼了?大不了買些口服蜂乳、桂元晶的花幾個錢!
」
柳月就笑了撇嘴:「你什麼時候來是帶了東西?哪一次來了又不是吃飽喝
醉?莊老師讓你去要符,總是給你說了腳傷吧,你今日探望病人又提了什麼禮
品?!」
孟雲房也笑了,說:「「你這小人精哪壺不開提哪壺,我沒給你莊老師拿
禮品,給你倒拿了一個爆栗子!」
指頭在柳月的腦頂上梆地一彈,柳月一聲銳叫,直罵孟雲房沒有好落腳,
天會報復了你的!孟雲房就說:「這話也真讓你說著!我那第一個老婆的兒子
從鄉下參軍了五年,是個排長兒,原想再往上升,幹個連長兒團長兒什麼的,
可上個月來信說部隊也讓他復員,而且是哪兒來的仍回哪兒去。
我那兒子就對首長說啦,報告團長,他們是兵可以從兒來的哪兒去,我是
排長呀!團長說:排長也是一樣。
我那兒子就說:「一樣了我就不說了,可我是從我娘的肚子裡來的,我無
法回去,何況我娘也都死了!」
柳月就破涕為笑,說:「真不愧是你的兒子!」
就又說道:「你有幾個老婆!聽大姐說,你前妻是城裡人,孩子才八九歲
,他當的什麼兵?!」
莊之蝶說:「柳月你不知道,他早年還離過一次婚,在鄉下老家的。」
孟雲房便說:「咱是有過三個老婆的人,一個比一個年輕!」
柳月說:「怪道哩,我說你臉上皺紋這麼多的?!」
莊之蝶瞪了一下柳月,問孟雲房:「孩子到底安排了沒有?」
孟雲房說:「我認識我老家縣上的常務縣長,打了長途電話給他,他答應
了在縣上尋個工作。
說出來你哪裡能想到,我在電話上說需要不需要我和莊之蝶回來一趟再給
地區專員說個情,莊之蝶和專員可是同學的。
他說啦,你這是拿大X嚇娃,要激將我嗎?你和莊之蝶還認識?我說不光
認識,他結婚還是我的證婚人!他就高興了,說莊之蝶是大名人,大名人委託
的事我能不辦?孩子安排是沒有這個政策,可我用不著暗中走後門,還擔心有
人告狀生事,我要公開說,這孩子是莊之蝶的親戚,就得安排,誰如果有親戚
能給社會的貢獻有莊之蝶那麼有影響,要安排個工作,我保證還是安排!」
莊之蝶說:「你盡胡成精,最後出了事都是我的事!」
孟雲房說:「這是你的名氣大呀!等那常務縣長到西京來了,我領他到你
這裡來,還要勞駕你招待一下他哩!」
柳月說:「哎呀呀,你來吃了,還要帶一個來吃!」
孟雲房說:「不白吃的,你瞧瞧這個!」
從懷裡掏一個兜兒藥袋子,讓莊之蝶立時三刻戴在小腹的肚臍眼上。
莊之蝶說:「你又日怪,腳傷了,在這兒戴什麼?」
孟雲房說:「你總是不信我。
一天光寫你的書,哪裡懂得保健藥品!現在以市長的提議,在城東區開闢
了一個神魔保健街,全市有二十三家專出產保健品了。
這是神功保元袋,還有神力健腦帽,神威康腎腰帶,魔功藥用乳罩,魔力
壯陽褲頭,聽說正研製神魔襪、鞋、帽子,還有磁化杯、磁化褲帶;磁化枕頭
床墊椅墊……」
莊之蝶說:「你甭說了,這現象倒不是好現象,不知是誰給市長出的餿主
意!魏晉時期社會萎靡,就興過氣功,煉丹,尋找長生不老藥,現在竟興這保
健品了?!」
盂雲房說:「你管了這許多!有人生產就有人買,有人買就多生產,這也
是發展了西京經濟嘛!」
莊之蝶搖了搖頭,不言語了,卻說:「這麼多天,我不得出門,也不見你
們來,我有一件事要給你說的。」
就讓柳月先出去。
柳月撇了嘴說:「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不告訴我,我向大姐告狀的!」
孟雲房就說:「你要聽話,過幾天我給你也帶個魔功乳罩來!」
柳月罵道:「你這臭嘴沒正經,你先給夏姐兒戴了再說!」
孟雲房說:「這女子!我老婆真戴了的,乳頭乍得像十八九歲姑娘娃一樣
的!」
莊之蝶說,「柳月還是姑娘家,你別一張嘴沒遮沒攔的。」
看著柳月出去了,悄聲道:「你提說的清虛庵那樓上房子的事,我給市長
談了,市長把房子交給咱們了,還配了一套舊傢俱。
這是鑰匙,你不妨去看看。
再叮嚀你一次:誰也不要告訴的,牛月清不要給說,夏捷也不能說!」
喜得孟雲房說:「這太好了!你到底是名人,比不得我們人微言輕,咱們
應好好寫一篇文章在報上發表,宣揚宣揚市長重視文藝工作。」
莊之蝶說:「這你就寫吧,以後需要人家關照的事免不了的。
有了房子,怎麼個活動你考慮一下,平日哪些人可以參加,哪些人得堅決
拒絕,但無論怎樣,鑰匙只能咱兩人控制。
等我腳好了,咱就開辦一次。」
孟雲房說:「第一次讓慧明講禪吧。
現在興一種未來學,我差不多翻看了中外有關這方面的書,但慧明從禪的
角度講了許多新的觀點,她認為未來世界應是禪的世界,是禪的氣場,先進的
人類應是禪的思維。
我也思考這事。
這下有了活動室,我可以去靜心寫了,在家夏捷是整日嘟嘟囔囔。
禪靜禪靜,我可沒個靜的去處!」
莊之蝶說:「真正有禪,心靜就是最大的靜了,禪講究的是平常心,可你
什麼時候放下過塵世上的一切?你還好意思說禪哩!我著你是又不滿足人家了
,你那些毛病不改,娶十個老婆也要嘟囔的。」
孟雲房笑著說:「這我又怎麼啦,我沒你那知名度,能碰上幾個女的?」
莊之蝶說:「我哪像你!」
孟雲房嘿嘿地笑,說:「你也是事業看得太重,活得不瀟灑。
我替你想過了,當作家當到你這份兒上已經比一般文人高出幾個頭了,可
你就能保證你的作品能流傳千古像蒲松齡嗎?如果不行,作家真不如一個小小
處長活得幸福!佛教上講法門,世上萬千法門,當將軍也好,當農夫也好,當
小偷當妓女也好,各行各業,各色人等,都是體驗這個世界和人生的法門。
這樣了,將軍就不顯得你高貴,妓女也就不能說下賤,都一樣平等的。」
莊之蝶說:「這我哪裡不清楚,我早說過作家是為了生計的一個職業罷了
。
但具體到我個人,我只會寫文章,也只有把文章這活兒做好就是了。」
孟雲房說:「那你就不必把自己清苦了,現在滿社會人亂糟槽的,有權不
用,過期作廢;有名不利用,你也算白奮鬥出個名兒。
不給你說有權的人怎麼以權謀私,這樣的事你也見得多了,就給你說說我
家隔壁那個老頭吧。
老頭做生意發了,老牛要吃嫩苜蓿,就娶了個小媳婦。
他的觀點是,有錢了不玩女人,轉眼間看著是好東西你卻不中用了。
剛才我來時,路過他家窗下,他是病三天了,直在床上哼哼。
我聽見那小媳婦在問:你想吃些啥?老頭說:啥也不想吃的。
小媳婦又問:想喝些啥嗎?老頭說:啥也不想喝的。
小媳婦就說了:那你看還弄那事呀不?老頭說:你活活兒把我扶上去。
你瞧瞧這老頭,病懨懨得那個樣兒,人家也知道怎麼個享受哩!」
莊之蝶說:「我不和你扯這些了,你最近見到周敏他們嗎?他也不來見我
!我總覺得有一個巨大的陰影壓著我的。
雲房,今年以來我總覺得有什麼陰影在罩著我,動不動心就驚驚的。」
盂雲房說:「你真有這麼個預感?」
莊之蝶說:「你說,不會出什麼大事吧?」
孟雲房說:「你沒給我說,周敏倒給我說了,我就等著你給我說這事的。
你既然還信得過我,我要說,這事不是小事,牽涉的面大,你又是名人,
抬腳動步都會引得天搖地晃的,周敏是惶惶不可終日,這你要幫他哩!」
莊之蝶說:「我怎麼沒幫他,你別聽他說。
他那女人還好?」
盂雲房詭笑了一下,低聲道:「我知道你要問她了!」
莊之蝶冷下臉說:「你這臭嘴別給我胡說!」
孟雲房就說:「我怎敢胡說?我去過他們那兒,卻沒見唐宛兒出來,周敏
說是她病了。
那花狐狸歡得像風中旗浪裡魚的,什麼病兒能治倒了她?!怎麼能不來看
你,這沒良心的。
莊之蝶是輕易不動葷的貓,好容易能愛憐了她,她一個連城裡戶口都沒有
的小人物,竟不抓緊了你,來也不來了?!」
莊之蝶從糖盒揀起一顆軟糖塞到孟雲房的嘴裡,孟雲房不言語了。
吃過午飯,莊之蝶在臥室裡睡了。
腦子裡卻想著孟雲房晌午說的話來。
原是多少在怨唐宛兒這麼些日子人不來電話也不來,才是她也病了!她得
的什麼病,怎麼得的,是不是那日在古都飯店沒有找著他,又給這邊撥電話撥
不通,小心眼兒胡思亂想,害得身上病兒出來,人在病時心思越發要多,也不
知那熱騰騰的人兒病在床上又怎麼想他?不覺回憶了古都飯店裡的枝枝節節,
一時身心激動,腿根有了許多穢物出來。
隨後,脫了短褲,赤身睡了一覺,起來讓柳月去把短褲洗了。
柳月在水池裡洗短褲,發現短褲上有發白起硬的斑點,知道這是什麼,只
感到眼迷心亂。
想夫人中午並不在家,他卻流出這等東西,是心裡作想起誰了?是夢裡又
遇到誰了?那一日她唱《拉手手》,他是拉她在身上的,她要是稍一鬆勁就是
婦人身子了。
那時她是多生了一個心眼,拿不准主人是真心地愛她,還是一時衝動著玩
她。
莊之蝶是名人,經見的事多人多,若是真心在我身上,憑我這個年齡,保
不准將來也要做了這裡主婦;即使不成,他也不會虧待了我,日後在西京城裡
或許介紹去尋份正經工作,或是介紹嫁到哪家。
但若他是名人,寵他的人多。
找女人容易,他就不會珍貴了我,那吃虧的就只有我了。
現在看了這要洗的褲子,雖不敢拿准他是為了我,卻也看透了這以往自己
崇拜的名人,不畏懼了也不覺害怕,倒認作親近了起來。
洗畢短褲,在院中的繩上晾了,回房來到穿衣鏡前仔細打量自己,也驚奇
自己比先前出落得漂亮,她充滿了一種得意,拉了拉胸前衫子,那沒有戴乳罩
的奶子就活活地動。
想著幾日前同夫人一塊去街上澡堂裡洗澡,夫人的雙乳已經鬆弛下墜,如
冬日的掛柿,現在一想起那樣子,柳月莫名其妙地就感到一陣欣悅。
正媚媚地沖自己一個笑,門口有人敲門。
先是輕輕一點,柳月以為是風吹,過會又是一下,走近去先上了門鏈後把
門輕輕開了,門外站著的卻是趙京五。
趙京五擠弄了右眼就要進來,門鏈卻使門只能開三寸長的口縫,趙京五一
只腳塞進來了只好又收口去。
柳月說:「你甭急嘛,敲門敲得那麼文明,進門卻像土匪!」
趙京五說:「老師在家嗎?」
柳月說:「休息還沒起來,你先坐下吧。」
趙京五就小了聲,說:「柳月,才來幾天,便白淨了,穿得這麼漂亮的一
身!」
柳月說:「來的第二天大姐付了這月工錢,我去買的。
這裡來的都是什麼人,我穿得太舊,給老師丟人的。」
趙京五說:「喲,也戴上菊花玉鐲兒了!」
柳月說:「你不要動!」
趙京五說:「攀上高枝兒了就不理我這介紹人了?」
柳月說:「當然我要謝你的。」
趙京五說:「怎麼個謝法?拿什麼謝?」
柳月就打了趙京五不安的手,嘻嘻不已。
會又開了三天,三天裡唐宛兒來過兩次,又約定了還要再來,喜得莊之蝶
精神亢奮,心裡也不多想了那文章引起的煩惱。
這天晚飯,餐廳的桌子上碰著了黃德複,倒吃了一驚!黃德複整個兒瘦了
一圈,原本白淨的臉幹黃如蠟,眼眶發黑,問是得了什麼病嗎?德複說:「困
的。」
莊之蝶就把要清虛庵那套單元樓房作文藝沙龍的請求讓他通融市長,給予
關照。
德複口裡應允了,卻直說不要太急,現在市長要辦的事多如牛毛,樣樣都
重要,一時是沒個時間來料理這等小事的。
莊之蝶說:「這能費了市長多少時間的,還需要寫書面報告,開辦公會議
研究嗎?你兩三句話一說就完了,人大的會議,市長不正好能趁機休息嗎?德
複說:「你們這文人,該怎麼說呢,你以為這種會議,領導就能休息嗎?」
就拉了莊之蝶到一邊,悄聲說,開人代會比打一場戰爭還緊張的。
會議前,他和秘書長每天晚上開車去郊縣和市內各區gov瞭解情況,找
人談話,該講明的就講明,該暗示的就暗示,他是囫圇圇五個晚上沒得睡覺。
會議期間,更是複雜得了得,原定的人事安排,是要換掉人大主任,但有
人私下串聯,偏偏還要選他,說不定最後那日選舉,他真要選票多當選了,事
情就糟了。
而市長的連任問題是不大,但如果票數雖過半或是過半不多,那不也是給
市長難看嗎?黃德複說:「這些情況你知道?」
莊之蝶說:「我哪裡知道?整個會議莊重熱烈,裡邊還有這麼多根根蔓蔓
的事!」
黃德複說:「你們文人不懂得政治也好。
可你想想,現在你要我立馬三刻給市長說房子的事,市長心緒好了事情或
許好辦,他正煩著,一個隨便的理由都能先否定了你,以後再也說不得了。
這事我見機行事,你放心,我不會壓著不辦的。」
一席話,的確是肺腑之言,卻聽得莊之蝶目瞪口呆,也不再提說這事。
再見到市長或黃德複滿面笑容地在樓廳裡與代表們握手寒暄,也不近去招
呼,遠遠離開,到自個房間去看書。
也就在這日下午,大會chair_man團通知小組討論,服務員就送
來了大會期間給代表訂的三份報紙。
發言的繼續發言,未發言的就翻開報紙。
莊之蝶先讀了省報第三面的文藝版,又看市報,幾乎一二面全是有關大會
的各類報導,覺得沒甚意思,就去讀第三份叫《周未》的報紙,一下子被一條
消息吸引。
消息的標題是:市府大院上班拖拉,半小時後來人過半。
內容竟是本報記者于X月X日上班時突然在市府門口作調查:上班後十分
鐘來了多少人,二十分鐘後來了多少人,半小時後來了多少人。
局長遲到的有幾位,副市長遲到的有幾位。
立時會上議論紛紛,話題由討論市長的gov工作報告變成了對此報導的
爭論。
莊之蝶聽了聽,無非是亂哄哄地發牢騷話。
覺得索然無味,就回到房間給家裡撥電話,詢問有沒有要緊事。
接電話的是柳月,直問「誰呀?誰呀?」
莊之蝶正要說話,電話裡卻傳來嘻鬧聲。
他想聽聽嘻鬧的是誰,便不說話,柳月在那邊說:「神經病!」
哢地把聽筒放下了。
莊之蝶再撥,柳月不問青紅皂白,吼道:「錯了,這是火葬場!」
電話又按了。
氣得莊之蝶又一次撥了電話,一等那裡拿了聽筒就罵道:「柳月,你在家
就這樣接電話嗎?!」
柳月聽清了聲音,忙說:「莊老師,怎麼是你呀?這幾天你不在,每日幾
十個電話尋你的,我說你不在的,過會兒電話又來,大姐就讓我接了說號碼錯
了。
倒沒想到竟誤了你的電話。」
莊之蝶還在發火:「誰在那裡和你說話!」
柳月說:「是洪江。
他是才來尋你的,你要給他說話嗎?」
電話裡就有了洪江的聲音,先是支吾不清,後來說到書店的事,立即說那
一部書稿已印出兩天了,發散到各地零售點,銷路十分地好。
洪江咕咕嘟嘟說了半天,莊之蝶沒吭聲,洪江就說:「莊老師,你聽著了
嗎?」
莊之蝶說:「嗯。」
洪江說:「這一次是撈住了,我大概計算了一下,咱們投資十萬,能純收
入三萬的!照眼下的行情看,我想過十天半月咱再印一萬,所以想是否招待一
下郵局發行科那個姓賈的?此人不敢得罪的,除了正經發行管道外,他手裡有
個黑道發行聯絡圖哩,如果你覺得這主意行,你是否能出面見見他,明天,還
是後天?」
莊之蝶說:「我沒空,你給你師母說吧。」
就把電話放了,拉展床鋪,一直睡到吃晚飯的時辰。
吃罷飯,去院門外看了看,沒有發現唐宛兒來。
大會安排晚上去易俗社看秦腔的,許多代表已三三五五結夥一邊散步一邊
往劇院去了,有人喊莊之蝶一塊走,莊之蝶說他得回家一趟,外地來了客人的
,推辭了。
待看戲的都去看戲了,回到房間等候約好的唐宛兒,卻想該拿什麼吃的招
待婦人,便才去商店買了一盒口香糖回來,黃德複卻敲門進來,說:「市長找
你呢!」
莊之蝶說:「市長找我?」
當下虛掩了門,兩人去至對面樓二層的一個套間。
推門進去,市長正歪在長沙發上吸煙。
一見莊之蝶,市長起身說:「大作家來了,這些天都在會上,你怎麼不來
見我?」
莊之蝶說:「你太忙,不敢打擾麼?」
市長說:「別人不見,你來能不見嗎?德複給我談了你的請求,要支持嘛
!有人說我是只抓文化,不抓政治經濟,該當文化部長而不是市長。
嘿,落了這麼個名兒,我倒真要為知識份子辦些實事。
清虛庵那套單元房,就給了你們吧,以後搞什麼活動,如果覺得我還可以
當個聽眾,別忘了通知我哦!」
莊之蝶從沙發上跳起來,說:「真謝謝市長了!市長抓文化,這是抓住了
西京的特點。
文化搭台,經濟唱戲,這怎麼僅僅是文化的事呢?別的行業中我瞭解不多
,在文藝界,你的政績可以說是有口皆碑!」
市長說:「德複,你把鑰匙交給之蝶吧。」
黃德複果然從口袋掏出房證和鑰匙,說:「市長心倒比我細,說你們去辦
理房證,又得到處尋人,作家的時間耽擱不起,今中午特意讓我去辦理了。」
莊之蝶接過鑰匙,真不知說些什麼好。
市長又說:「你們文藝界以後還有什麼事就來直接找我,聽說西京城裡有
四大名人,我倒只認識你莊之蝶和阮知非。
德複呀,你揀一個星期天,把他們四大名人召集在一塊,我請他們吃頓飯
,交交朋友!」
黃德複說:「這太好了,周恩來總理一生就喜交文藝界朋友,他說過,一
個政治家沒有幾個文藝家朋友就成不了什麼大政治家。」
市長說:「這些人都是市寶嘛!古話說,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
我這市長,今日當了今日是市長,明日不當了我什麼也不是。
你們卻不同了,有了好的作品,千古留名的!」
莊之蝶笑著說:「市長也太謙虛了,幹我們文藝這一行畢竟是虛東西。
上個月我去六府街口。
見那裡修有一座水房,牆上紅漆寫了六個大字:「吃水不忘市長!我就感
觸極深,真正千古留名的都是給百姓辦了實惠事情的。
現在杭州的白堤、蘇堤、甘肅的左公柳就是明證。」
市長哈哈笑了,說:「六府街口那兒一直沒有通自來水,尤其是夏天,居
民盆盆罐罐要到三裡外的別的街巷去提水,群眾意見很大。
我知道這情況後,把城建局、自來水公司的領導叫來,讓他們說說是怎麼
回事,當然他們有許多實際困難。
我就發火了,不管你說一千道一萬,西京這麼大個現代城市竟然還有一塊
沒水吃?!必須十天之內水要到那裡,如果第十一天我去那裡發現還沒有水,
誰的責任我就撤誰的職!水果然第九天就通了。
那日幾千人在那裡敲鑼打鼓,鳴放鞭炮,還做了匾要送到市gov來。
我知道了,趕緊讓德複去制止。
我心裡在想,老百姓太好了,只要你真正為他們辦一點事,他們會永遠忘
不了的!」
莊之蝶說:「哎呀,這麼好的題材,我們文聯應該組織一些人去寫寫!」
市長說:「這你們不要寫,它牽涉到個人的事。
這裡倒有一篇文章,是下邊一些同志寫的,送到我這兒讓我過目,我看了
覺得還不錯的。
據說省報準備刊發,但什麼時候發,就說不準了,聽他們說,現在風氣不
好,連par_ty報刊發文章也得有熟人,真是豈有此理!」
市長說著,就取了一遝稿件給莊之蝶,說:「你看看。」
莊之蝶收了,市長便說:「這樣吧,德複你和大作家到你的房間去看吧,
我再過三分鐘還要去市委開個會的。
之蝶,改日我去你房間聊吧,你住七零三房間?」
莊之蝶說:「你要有空,你打電話我下來就是了。」
兩人又到了隔壁房間,黃德複關了門,說:「你先看看稿件。」
莊之蝶看了,文章的題目是:「市長親自抓,改革作先鋒。
副題是:西京市府大院的新風氣。
內容幾乎是從另一個角度來針鋒相對了《周未》報的批評。
黃德複說:「今日《周未》上的文章你看到了吧,那是有人在搞政治陰謀
。
這樣的文章原本是該發在市報上的,但偏偏發表在《周未》,他們的目的
很明確,就是選舉前詆毀市府工作。
這篇文章影響極壞,經查,就是那個人大主任手下人寫的。
上午我們趕出這份稿子,決定省市兩家par_ty報同時發出,市報當
然無誤,只是省市兩報常鬧彆扭,一向不大好好配合;而省報是省上的,咱市
上卻無權管得了人家。
你在省報那兒認識人多,這你得出面,一定要他們保證明日刊出來,又必
須在頭版頭條。
你覺得要給什麼人打招呼,由你決定,花錢的事你不要管,哪怕咱幾萬元
買下他們版面來也行。」
莊之蝶說:「熟人是多,可明日刊出,這來得及嗎?」
黃德複說:「後天就要選舉,只能明日刊出來,這就看你的本事了!今晚
車已經派好,我陪了你去。」
莊之蝶說:「那好吧,現在尋主編已來不及,編排室主任是我的朋友的哥
哥,讓他抽下別的稿子,把這篇塞進去。」
便寫了一些人的名字,要求給人家買些禮品什麼的。
黃德複即刻委託了人出去採買電鍋、烤箱、電子遊戲機一類東西去,說:
「今晚可是稿子不發咱就不回來啊!」
莊之蝶卻面有難色了。
黃德複問:「你晚上有事?」
莊之蝶說:「倒也沒什麼事,這樣吧,你在這兒等我,我去我的房間取個
包兒。」
黃德複說:「我跟了你去,你是名人,找你的人多,說不定一去又碰上什
麼人纏住了身。」
莊之蝶心裡叫苦不迭,只好說:「那我就不去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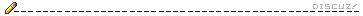
飘蓬春海意嗟吁…… |
|


